
邮箱 :news@@cgcvc.com
文章来源: 发布日期:2023-0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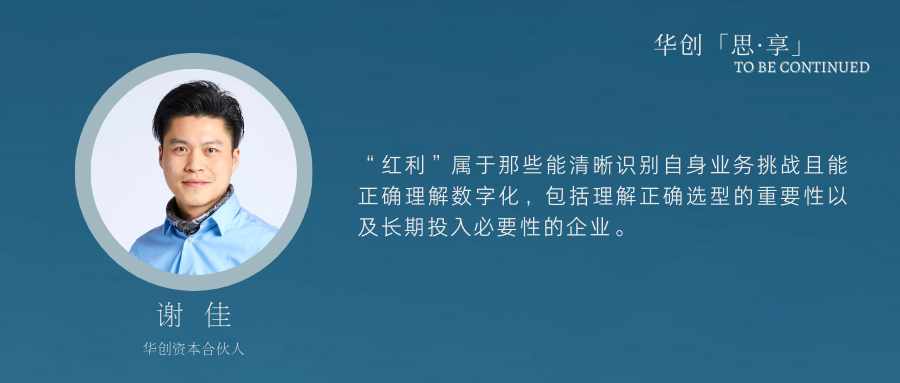
文 | 数字时氪
数字化浪潮正在影响全产业发展。
在国内,产业数字化的经济规模占全国数字经济比重的81.7%,占中国GDP的32.5%,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
数字化与产业的融合越来越深,但经历疫情三年,各产业都受到不用程度的影响,产业数字化在新的阶段下如何发展?2023年,数字化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近日,36氪数字时氪对话华创资本合伙人谢佳,聊了聊他对2023年数字化的展望:
“红利”属于那些能清晰识别自身业务挑战且能正确理解数字化,包括理解正确选型的重要性以及长期投入必要性的企业。
我期待看到这些企业可以更多地尝试利用云数据分析工具将数据价值发掘出来。
我想,在国内我们发展各个领域底层基础技术就特别需要类似这样社会化的、市场化的、有远见的、或甚至是“适度愚蠢”的长期主义长线资金来支持创新。
以下部分为专访部分(经数字时氪编辑):
Q:很多人认为,重大的群体性灾害、灾难、变故后,全社会的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您的角度来看,疫情三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数字化的理念是否发生了一些系统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会如何影响中国数字化的趋势?
谢佳:值得指出的是,疫情三年我们同时也经历着全球政治环境、经济周期的显著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庞大的产业,例如汽车产业,在经历着轰轰烈烈的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各行各业的优胜劣汰也普遍变得更为残酷。
我的观察是,企业经营者对于经营效率以及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敬畏和警觉。对于企业经营者、决策者而言,他们一定是把企业的生存与业务发展放在首位,而不是抽象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国数字化的发展而言,过去三年经历的重要意义在于,更多的企业决策者开始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回答诸如“如何提升竞争力?”、“如何应对不确定性?”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相信这个影响会是深远的。
Q:疫情前后,中国对于数字化的价值判断是否发生或者会发生变化?具体是什么?
谢佳:最重要的变化可能在于,甲方和乙方都在进步,这与疫情未必直接相关,经历过去几年的数字化尝试与试错,越来越多的企业需求方能更好的回答“为什么需要数字化”,也有越来越多的软件供应商能更好的回答“怎样的数字化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什么问题”。
Q:疫情因素后,有人认为,中美在数字化的需求上呈现了不同的现象和趋势,您怎么看?如果是有差异,这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行业影响?如果是一致的,背后是否有共性的因素?
谢佳:中美市场的企业数字化发展可能从来都没有同频过,这两个市场的差异并不是简单的落后多少年可以回答的,因为行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同,美国市场的企业数字化发展经历了数十年的过程,处于有序的成熟发达阶段,市场认可数字化的价值、奖励数字化的创新,类似于沉积岩,随着理念与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企业数字化一层接一层的有序发展。
而中国市场的企业数字化发展更为碎片化与多样化,时代推着企业发展,大部分情况下缺少良好的顶层设计,因此局部系统也更容易被企业选择重建,类似于岩浆岩,可能一层还没完成冷凝,新的一层就又涌现出来,这同时也是早期市场的特点。
长期来看,尽管中国市场的企业数字化可能仍然不会像美国市场那么有序,但是对数字化价值的认可一定会趋近于美国成熟市场的水平。
Q:对企业而言,2023年中国的数字化是否有红利,红利可能是什么?
谢佳:无论对于实施数字化的企业方还是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在数字化之路上,我们可能很难期待看到某种短期的“红利”,因为数字化是一个前期看不到效果,并且需要持续投入不菲的成本、资源和管理决心才有可能看到后期显著回报的持续经营活动,而不是某种短期项目。这个过程中还很有可能因为路线方案选择错误,或是管理能力跟不上先进理念导致的失败。
“红利”属于那些能清晰识别自身业务挑战且能正确理解数字化,包括理解正确选型的重要性以及长期投入必要性的企业。越早这么干的企业就能越早展现出“数字化”带来的市场竞争力。抛开这些前提来谈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焦虑,或是政府鼓励扶持数字化的政策红利,很有可能导致的是企业的“数字化债务”而非“数字化红利”。
Q:在当下,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后,可以明显看到体制内的数字化的预算会更充裕,这会对中国整体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什么影响?
谢佳:我的理解是,数字化所追求的目标是组织机构的全面效率提升进而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因此,无论对于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化企业还是非盈利性的政府机构,数字化都能发挥其价值。具体来讲,数字化预算ROI最高的应用场景是那些追求效率的业务,否则,数字化并不是最合适的方式。作为数字化浪潮的一份子,我们当然很高兴看到不同行业领域对数字化的重视,充裕的预算必然会加速中国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数字化是中长跑,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投入以及持续进行数字化经营的决心,不能只看一年两年的短跑冲刺成绩。
Q:此前,大部分企业为数字化的投入动辄千万甚至数亿或数十亿元,如何看待这样的数字化增长和红利,未来这种模式是否持久?
谢佳:过去,大部分企业在IT建设方面的投入属于企业的“信息化”阶段,主要解决企业组织内部管理的基本问题,包括ERP系统、OA系统、财务管理系统、HR管理系统等等内部管理系统的建设,一些涉及复杂业务流程的,例如ERP系统,实际上能落地的主要是基础功能部分。
“信息化”建设的特点有些类似于传统软件的收费方式,对于企业而言往往是一次性购买投入,也方便做预算。而我们所讲的企业“数字化”阶段,是“信息化”之后的高级阶段,“数字化”的范畴覆盖到企业的业务本身,从设计到生产过程再到营销活动和销售售后管理的跨职能协作,全面收集和发掘企业在各项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数据价值,是一套活的系统。这样的“数字化”建设不可能是一次性投入就能实现的,涉及的长期整体投入与“信息化”建设也不是一个量级的。最关键的是,企业需要正确理解“信息化”建设与“数字化”建设节奏的差异。
Q:2022年36氪的访谈中,关于谁应该为数字化负责,呈现了2种观点:一把手工程、CIO/CDO , 您如何看?2023年行业会有哪些因素导致数字化负责人的变化?
谢佳:前文提到过“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差异,“数字化”的主线面向企业的业务,因此往往也模糊了过去企业所设置的部门边界。
“数字化”也一定是企业的“一把手工程”,不仅仅是因为在数字化建设的初期需要一把手的业务远见与洞察力来重塑企业的业务流程,数字化建设更重要的是部署完软件系统之后的运营阶段,让大家把系统用起来,因此更需要一把手的领导力来带动跨部门的协作,从高管到中层再到基层全员对数字化转型的反馈与支持,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一把手的及时决断力也是保证企业数字化往正确方向动态调整的关键。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数字化转型失败案例会让企业意识到数字化的“一把手工程”属性。
Q:当下各种数字化新产品更是层出不穷,在您看来有什么关键要素是“好产品”一定要具备的么?2023年有什么看好的数字化的相关服务或者产品?
谢佳:好的软件产品根本上是孕育自好的需求市场,中国市场目前极少出现品类定义级的软件产品,即便在CRM产品与HR产品这样的大品类,市场规模还不足够大,鲜有足够好的产品口碑出现。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软件企业不足够优秀,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的企业需要解决的商业问题和管理问题过于多样化、个性化,软件产品能直接解决的问题范畴有限。
对于软件企业和软件领域的投资人而言,我想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我一直相信,好的软件产品的灵魂一定是先进的思想,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问题或是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这个判断放到当下的中国市场需要加一些限制条件,可以修改为“恰当先进的思想”,因为处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过程中最需要的是既能解决眼前业务问题又具备合理顶层设计能力的软件产品与服务。
Q:2022年,国内外您觉得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数字化创新案例?2023年,您最期待看到哪方面的数字化创新和增长?
谢佳:几乎各个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企业都会主动尝试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一些行业本身就处于转型阵痛阶段背水一战的企业更是将数字化转型当作救命药丸。
务实的来看,在企业坚持长期投入的前提下,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显著地提升竞争力,但是再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也无法帮助一家传统企业成为一家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与数字化转型是两种不同的任务。
站在2023年看中国企业的数字化建设,经过过去数年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完成了关键业务环节的数据收集与梳理,我期待看到这些企业可以更多地尝试利用云数据分析工具将数据价值发掘出来,这个领域的产品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成本控制也越来越优化,倘若企业能进而探索数据管理与业务价值的结合,在数据科学家、数据工程师方面继续投入,一定可以看到回报。
Q:2023年,中国相比于欧美的公司,在数智化创新方面有什么优劣?
谢佳:过去十年是中国软件产业从“服务型”向“产品型”发展起步的关键阶段,涌入了大量的创业人才和充分的风险投资资金,这十年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取得突破的关键阶段。
因此,对于成长于过去十年的中国软件企业而言,将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融入软件产品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是件比较自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中美是同步的。得益于中国消费互联网轰轰烈烈的发展,我们具备了AI应用技术的完整能力,但相比欧美市场,我们在底层基础技术能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所有前沿技术的应用市场发展都取决于其底层基础技术的突破,往往没有底层基础技术的突破,应用的可用性就是零。
最近OpenAI ChatGPT取得的产品体验突破以及创造记录的用户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OpenAI在底层大模型算法方向的长期坚定投入是ChatGPT取得成功的关键。OpenAI很幸运,作为非营利机构在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来自于成功企业家、投资机构和巨头企业十亿美金级的资金支持,得以坚守长期主义而不受短期商业化压力的干扰。我想,在国内我们发展各个领域底层基础技术就特别需要类似这样社会化的、市场化的、有远见的、或甚至是“适度愚蠢”的长期主义长线资金来支持创新。
